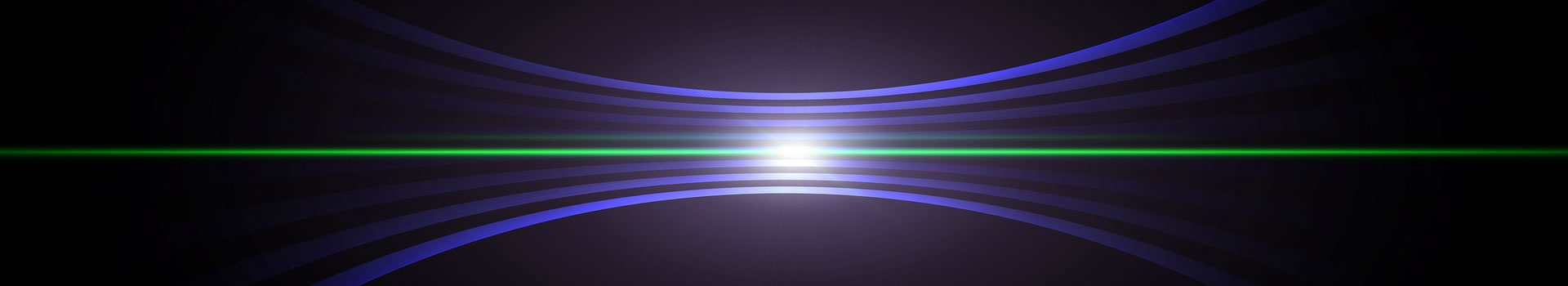

他作为“枪手”紧急被中宣部召回京。
舒芜,1922年诞生于安徽桐城的世家望族,自幼便沐浴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中。他原名方管,初涉文坛时,以“舒吴”为笔名,此名源自桐城方言中“虚无”的发音。然而,舒芜认为“舒吴”不够像人名,遂将其更改为“舒芜”。1942年春,二十岁的舒芜告别故土,前往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担任助教。彼时,他深受墨家学说与古代哲学思想的浸润,致力于纯文学的研究。他先后在《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上发表了《释无久》一文,探讨“无久”即时间不存在或长度为零的哲学议题,随后又撰写了《论因果》、《论存在》、《文法哲学引论》等哲学论文,展现了他扎实的学术功底。在此期间,舒芜通过青年小说家路翎结识了比自己年长二十岁的胡风。
舒芜结识胡风之后,便将所撰《论因果》等文章赠予其审阅。尽管胡风认为舒芜的文字“稚嫩、杂乱、艰涩”,他却仍不吝提携这位初出茅庐的学者,将他的作品推介至《文风》、《中原志杂》以及《中苏文化》等知名刊物发表。胡风还特意将《释无久》一文介绍给同是墨学研究的陈家康(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鉴赏,并致信舒芜,针对其研究方向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建议舒芜不宜过分专注于纯学术研究,而应将目光投向现实的文化议题,因为这“尤为迫切”。此后,舒芜开始关注社会议题与意识形态,并在胡风的引荐下,结识了陈家康、乔冠华等党员作家。胡风无疑成为了舒芜的恩师,也是其学术道路上的指引者。
1942年上半叶,舒芜完成了《论主观》一文。尽管胡风对该文的部分观点持有保留意见,但他仍将其刊登于他于1945年1月创办的《希望》杂志上。由于《论主观》过度推崇主观因素,推崇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因此遭到了黄药眠、邵荃麟、乔冠华等人的公开批判。在1945年7月2日致胡风的一封信中,舒芜写道:“观察朋友们对此的反应,我似乎正逐渐滑向市侩主义。”
1947年,舒芜告别了重庆,踏上了前往广西的旅程,开始在南宁师范学院授课。翌年,随着广西的解放以及南宁师院迁址桂林,舒芜肩负起南宁中学校长的重任,并身兼数职:广西省人大代表、广西文联研究部长、南宁市文联副主席以及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尽管如此,舒芜对长期驻留这个偏远城市心生不甘,遂致信远在上海的胡风,寻求帮助。广西方面依然对他寄予厚望,委以南宁市中小学校教师寒假讲习班副主任之职,并实际参与领导当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众多省市领导纷纷来到讲习班发表演讲,舒芜在指导他人学习的同时,也全神贯注地聆听。他在给胡风的信中提及,在老干部身上,他看到了毛泽东思想的生动体现。胡风在回信中也勉励舒芜,要“以老干部的理论为指导,解决实际问题”。
1950年十月,舒芜赴北京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举办的会议,期间与胡风及路翎(彼时担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编剧,后因胡风事件被捕,入狱长达二十年)重逢。彼时,对电影《清宫秘史》的批判已拉开序幕,文艺界及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亦如火如荼地展开,一场“人人过关”的运动势在必行。
此后,舒芜陷入了自我反省与对他人的批判之中。他坦言:“人的思想往往难以摆脱外界环境的熏陶,彼时国家正值如此,我们便应顺应国家的发展方向。”
舒芜自北京返程后着手创作了《与错误决裂》一文。1951年12月4日,他在邕宁县参与土改试点时偶遇了北京文艺界土改工作组成员、编剧鲁煤,遂将手稿呈上,称系为思想改造所作。鲁煤审阅后认为不妥,认为不应全盘否定自己的过往作品与思想。他致信北京友人徐放,表达了对舒芜做法的不认同,并建议胡风深入了解舒芜。鲁煤还建议将此信转交给胡风。胡风迅速回信,指出舒芜“常从表象入手,以观念推演……新观念变化剧烈,全盘否定过去”,“似乎意图以他人之血洗净自身”。尽管如此,舒芜仍感内心轻松,认为仅写万言书不足以应对如此重大问题,认为自己有必要作出更全面的交代。(摘自《舒芜口述自传》)
1952年5月25日,舒芜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章的头一句便说:现在很多人不重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吕荧(著名美学家,毕业于北大历史系,时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在讲课时把毛泽东的“讲话”作为最后一章来讲,还说:“我和路翎还有几个人……有共同的错误,是跟胡风理论上拘泥的倾向很相适合。”当时吕荧正在接受“思想改造”,见到舒芜点了自己的名,就一气之下辞了职。舒芜这篇文章被认为是他“反戈一击”的开始。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了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胡乔木的注意,指示《人民日报》于6月8日全文进行了转载,并根据舒文“还有几个人”加上了按语,指出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资产阶级文艺集团”。这就为以后对胡风的批判描绘了雏形。舒芜事后说:“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老实说也有点儿后悔,觉得毕竟搞出了一个‘小集团’的概念。”
胡风对舒芜的这种做法深表不满,说他“无耻”,你检讨自己的思想问题好了,干吗把别人也拉扯上,还把这些人都推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对立面?这种方式实在太可恶了!他在给路翎的信中谈到:“曾由武汉转信给他(指舒芜),要他深入地写一写,他就这样‘深入’了。”紧接着,舒芜在6月22日的《文艺报》上发表了《致路翎的公开信》,又点了他的老朋友路翎、吕荧、胡风等人的名:“路翎,作为一个曾在错误的道路上同行了好久的老朋友,我写这封信给你……还有几个人,曾经具有相同的思想。路翎就是一个。”胡风批驳这封信说:“看了以后,觉得意外。在我的理解上,他所说的理论问题不但混乱得很,而且也是和我连不上的。对路翎同志的批评,在我看也是和路翎同志连不上的。”
1952年7月,胡风接到了周扬的通知,要求他从上海赴京,以参与“文艺思想问题”的讨论,并加入全国文联的整风运动。
舒芜的文篇问世后,立刻引起了胡乔木、周扬等人士的关注,他们视舒芜为一位颇具文采的“笔杆子”,遂作出决定,将他调入京城。当舒芜于九月告别南宁之际,广西省委宣传部的高层领导曾力邀他留下。然而,舒芜却坚定地选择北行。对他而言,摆脱“边陲之地”的束缚,实现北上的夙愿,已是他长久以来的期盼。
行经武汉之际,舒芜向他的老友曾卓(“七月派”知名诗人,曾因胡风事件被捕入狱)坦言:“北京对胡风已是束手无策,这次邀我前去,便是要充当医生,施行手术!”舒芜抵达北京后,便即刻参与了由周扬主持的旨在“帮助”胡风的会议。会议将舒芜所撰写的《向错误告别》一文分发给与会代表。这场“帮助会”自九月持续至十二月,共举行了四次。胡风表示:“各位的帮助我深感欣慰,然而,我仍需逐步吸收。”
1952年12月27日,舒芜给胡风写信,“那篇文章(指《向错误告别》),回去后将重写。因为大致是要发表的,将只检查自己。那篇文章对你们提的意见,则想着只几个人看看的性质,所以尽所能理解的写出来,其中不对的地方一定有,仅提供参考”。胡风后来说:“他安详得很,这是转过头来用笑脸把我也当做小孩子看待了。”
在批判会期间,舒芜遵照林默涵的指示拜访了胡风,两人于一家小酒馆共进晚餐,随后前往天坛公园进行深入交流。胡风质疑:“我们以往的理论究竟失误在何处?”舒芜坦率地分享了自己的见解。夜幕降临,两人依依惜别,这成为他们之间最后的“友好会面”。
舒芜在批判胡风之际,亦与中宣部领导商定条件,得以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编审一职。转眼间,半年时光过去,三十一岁的舒芜携家带口,正式迁往京城。这一举动,预示着一场悲剧的开始,不仅关乎他个人的命运,亦牵连到众多人的悲欢离合。
胡风当面斥责为“混账”。
舒芜日益显露出其“积极性”,这使得胡风对这位“忘年交”的友情日渐淡薄。1954年5月,胡风致信中央,对舒芜进行了尖锐的指控,称其“为市侩主义者,品质恶劣,欺骗之徒”,指出他在被捕并被开除党籍后,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党立场,成为党内破坏分子,“对解放军和老干部充满强烈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胡风在指控中首先引用了舒芜的私人信件和谈话内容,作为其“反党”行为的证据。尽管胡风蒙受冤屈,值得同情,但将他捧为无可挑剔的“圣人”亦是不公。同年7月27日,胡风提交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后简称“三十万言书”),在其中阐述了自己对新中国成立后文艺问题的看法和立场,认为文艺家受到“五把理论刀子”的制约,其中不乏对主管文艺工作的中宣部部分领导人的批评,并指出“利用叛徒(指舒芜)在党和群众面前公开散布谣言,污蔑那些不屈服于他的作家”。中央将此报告退回中宣部处理,中宣部认为该报告错误且反动,随即组织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二百余人召开八次会议批判胡风。唯有路翎为胡风及其自身进行了辩护。12月8日,联席会议闭幕时,周扬在会上发表《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宣布胡风与他的学术思想和文艺理论之间的分歧已演变成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阶级斗争。
尽管舒芜并非主席团成员,他却以“枪手”之姿参与了与胡风的直面交锋,此举令胡风怒火中烧。他未曾料到,这位与他有着深厚友谊的盟友竟会如此决然地“起义”。
舒芜在其自传中记载了胡风曾当面羞辱他的经过:在“批胡”运动的高潮时期,民主人士何剑勋从重庆来北京参加某次会议,特地前往人民文学出版社拜访友人聂绀弩(时任该社副总编辑),在院子里偶遇舒芜。三人共进晚餐于地安门,席间,聂绀弩提及胡风住处邻近,何剑勋便提议:“那我们去探望他吧。”舒芜稍作迟疑后,亦随同前往。抵达胡风家中,胡风夫人梅志见到舒芜时,显得有些惊讶,未料这位“夙敌”竟会造访自宅。胡风自客厅走出,仅言简意赅地三句,首句是与何剑勋握手时所说:“开会啊,尚有数日逗留,他日再行细谈。”言罢转身步入屋内,边走边对聂绀弩抱怨:“老聂,你竟不先行告知一声,竟引这等人物至我处!”接着又转身对舒芜斥责道:“我这地方,岂是那些无赖之徒所能随意出入的!”说罢,便径自入内。胡风在当日的日记中记载:“绀弩引无耻之徒及何剑勋至此,遂怒斥其出门。”
舒芜几个人那天尴尬地离开胡家,到北海喝茶。舒芜说:“这真是奇怪得很,胡风怎么这个态度呢?何至于生这么大的气?”聂绀弩说:“胡风气就气吧,你检讨就检讨,不该把他也拉上。”又说:“他当初发表你的《论主观》是为了批判的。”舒芜一听很生气,说:“怎么是这个说法呢?要是这样讲,那好,他给我的信都还在,可以拿出来证明嘛,看看当初是不是为了批判。”聂绀弩赶紧劝他说:“你在气头上,这种事,非同小可,冷静了再说。”聂绀弩特地让爱人周颖去告诉梅志,说舒芜可能要把信拿出来。在舒芜心目中,胡风的信件或许是他的一种“秘密武器”。既然是武器,迟早会被“枪手”打出去的。尽管舒芜曾声明这时想“拿信”和1955年的“拿信”不是一回事,但毕竟最终还是“拿”出去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思想文化领域风云变幻。1955年1月20日,中宣部向党中央呈交了关于开展胡风思想批判的专项报告。然而,当时党中央仅将针对胡风的批判定位在“思想斗争”的范畴之中。《文艺报》与《人民日报》相继刊登了批判性的文章。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胡风撰写了《我的自我批判》一文。
舒芜身为“胡风派作家”中首位公然自我批判及批评同道的先锋,当时他心系的是如何迅速与日渐式微的“胡风派”划清界限,以期在动荡时局中稳固自己的立足点。1955年4月13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一文,这篇作品标志着他从对胡风持有“拘泥倾向”的看法转变为“反党反人民”的论断,同时也见证了舒芜在批判胡风问题上的思想转变。此时,肩负起“批胡”重任的《人民日报》和《文艺报》早已察觉到舒芜的潜力,认为他在批判胡风一事上大有可为,于是便精心策划,主动邀请他投稿。
他的炮弹让胡风丧命
紧随其后的,便是那闻名遐迩的“交信事件”。尽管后来众人对该事件的细节叙述各有千秋,但总体上的经过依然脉络清晰。
林默涵回忆道:“大约在1955年5月的一个日子,舒芜莅临中南海中宣部办公室,将一封精心装订的胡风亲笔信交至我手,信中所述诸多事宜,他认为值得一看。”林默涵原本认为这些私人信件并无太多可取之处,便将其搁置于书架之上。然隔时日偶然翻阅,方察觉信中诸多对党内及非党作家充满仇视的字眼,其中许多暗语令他费解。于是,他再次请来舒芜,请求对信中不易理解之处加以注解,并对信件内容进行分类整理。舒芜同志迅速完成了整理工作,并在一两天后将整理好的信件交还给他。林默涵阅后将其转交给了周扬。周扬在仔细阅读后,与我商讨是否可以公开发表,我表示赞同。随后,周扬将相关材料交给《文艺报》,待清样排出并附上主编的按语后,又将材料转呈毛主席。(参见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由此可知,舒芜曾两次前往中宣部,亲自将胡风信件交付给林默涵。
而舒芜就“交信”一说却给出了另一种版本:“我可以确切地说明一下,所谓‘交信’,根本就不存在。我从来就没有向任何人交过什么信。当时,只是《人民日报》编辑叶瑶奉命给我出了一个‘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这个题目,她向我组稿,我觉得宗派主义这个问题,在当时批判胡风已经达到的程度上,是个‘不上纲’的次要问题,而且也符合我对胡风早就已有的想法(觉得他太孤立自己),所以就接受了这个约稿。我所指的宗派主义,主要是指胡风对于文艺界许多人一概过于否定,过于蔑视。这在他的公开文字中表现得还比较含蓄,在私人通信中就说得很明显。我的文章要说清楚这一点,就不能不引用胡风给我的信。《人民日报》要发表我的文章,叶瑶为了核实我文章中所引用的胡风给我的信的原文,向我借信去校对,是借用一下,我就借给了她。‘借出去’和‘交上去’这两个性质上完全是不一样的。”他还说:“……完全是《人民日报》当时的文艺组长袁水拍他们,背着我,叶瑶其实也不知道,把信交到林默涵那里,结果搞得不可收拾。等到林默涵从袁水拍手里看到了这些信,那就等于给公安部看到了,我想捂也捂不住了。他(林默涵)找我谈话,我当然不敢反抗了。既然林默涵发了话,我就不敢不按照他的‘指示’编出了那个材料……”(《舒芜口述自传》)
当时,“肃反运动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文艺报》的常务编委康濯所提供的信息,对林默涵的陈述给予了有力佐证。同时,《人民日报》的编辑叶瑶所揭露的情况,亦为舒芜的观点提供了支持。
四位当事人的证言出现了二比二的局面。到底是谁充当了这个信使的角色,也许永远是个谜。不过,这对于整个案件的进程似乎并不重要,信件到了上层领域并进入运作才是关键的。林默涵得到信件后约舒芜在办公室谈话,对他说:“你的文章(指《胡风的宗派主义》)和胡风的信,都看了。你的文章可以不必发了。现在大家不是要看舒芜怎么说,而是要看胡风怎么说了。”林默涵要求舒芜将他在信上画记号的地方摘下来,按内容分为四类:胡风几十年来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我们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怎样一贯反对革命文艺队伍,怎样进行反党宗派活动,其宗派活动以怎样一种思想和世界观做基础。舒芜“回来大约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按照林默涵同志给拟定的四个小标题,进行摘录、分类、注释”,写成后来改的题目《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交了上去。此时的舒芜已经上了“战车”,身不由己。
林默涵与周扬经过商议,最终决定在《文艺报》上刊登这批材料,同时发表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随后,由《文艺报》常务编委康濯执笔撰写了“编者按”,其中依然将胡风的问题归结为“文艺思想和作风问题”,并期望他能够“检讨并改正”。周扬认为,“胡风的检讨以及舒芜的材料,最好还是呈送给主席审阅”。于是,在5月9日,他将稿件清样呈送给了毛泽东,并附上了一封信。翌日,毛泽东回了信。
周扬同志:
文本略有瑕疵,已进行相应修改。敬请陆定一同志审阅,若认为适宜采用,请另行誊写并退还原稿。若意见不合,请于今晚十一时之后或明日午后,至我处商议。稿件可刊登于《人民日报》,随后在《文艺报》上转载,按语需使用较大字号。
毛泽东五月十一日
周扬看到,这个材料的原题中“胡风小集团”,改成了“胡风反党集团”,并推翻原来按语,由毛泽东亲自写了一个八百字的编者按,并说:“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他在按语中号召向舒芜学习,“交出与胡风往来的密信”。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舒芜所撰写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随后,陆续发布了第二批、第三批材料,揭示了胡风“追随者”们被迫上交的158封信件,并将“反党集团”的称呼改为“反革命集团”。这些材料被汇编成册,毛泽东亲自撰写了《序言》,总印数达七百六十多万份,分发至全国各地,使得对胡风思想的批判转变为一场政治上的对敌斗争。舒芜所提供的信件及批判文章,犹如引爆“重磅炸弹”的导火索。众人纷纷对这位突然崭露头角的“黑马”投以关注,舒芜顿时成为全国范围内的焦点人物。
周扬感慨道:“未曾想,主席竟会以如此方式转变性质。”
舒芜感慨道:“未曾料想,胡风竟因此沦为反革命。”
胡风览阅《人民日报》的内容,不禁愕然。他感慨道:“未曾料想事态竟演变得如此严重,后果不堪设想,恐将波及无数人!”
1955年5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对胡风及其“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核心成员实施逮捕。与此同时,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长沙等地,对涉嫌“胡风案”的分子进行收审的行动亦同步展开。审判员们不约而同地鼓动“胡风分子”效仿舒芜,选择“起义”,揭露“同党”。在此过程中,两千一百余人受到了牵连并被拘押,最终被正式认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的有七十八人。舒芜对此感到惊恐不安,他坦言未曾料到事态会发展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
“胡风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不懈追求进步的一生,是满怀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并致力于文艺事业贡献的一生。”
在胡风出狱直至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间,众多“胡风分子”以及他们的同情者纷纷前往探望胡风及其家人。然而,在这份长长的探视者名单上,却始终未见那位近在咫尺的舒芜的名字。
他被控歪曲胡风信件。
胡风先生离世之际,对该案件的深刻反思与对舒芜先生的诸多质疑如潮水般涌现。
了解情况的当事人提出一个“道德底线”问题,他们一致认为,此前没有任何人存心要把胡风置于死地,也就是说,一直到舒芜“交信”为止,胡风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畴”,尽管已到了危险的边缘。这个冤案的发生、发展固然有其复杂的政治背景和极左因素,但导致对胡风批判升级和性质转变的直接原因,则是从舒芜提交的私人信件开始的。胡风夫人梅志及其子女也说:舒芜擅自公布受宪法保护的私人信件已属“违法侵权”,私信说的自然都是个人的看法,有些可能会激烈一些,也不可能深思熟虑,有很多的事实根据。可是一被拿出来,加上别有用意的注释和按语,又由于是摘录,这样就为曲解原意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舒芜在这“两天两夜”里又“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文字创造力”,运用了“歪曲事实、移花接木的手法”,经他“摘编”而成的文章是“建国后一大冤狱的发端”。
通过阅读《胡风全集》第九卷中的“书信”部分,我们能够发现,该卷完整收录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中摘自二十九封信件的全部三十四则引述。参照《胡风全集》的编者注释,我们能够清晰地洞察舒芜所展现出的非凡“创造力”。
因为信件是胡风写给舒芜的,所以舒芜便是信件的“权威”解释人,他说的话别人不能不相信,包括毛泽东在内。作为最高领袖,毛泽东不可能对舒芜提供的材料一一核实,于是他才写下了这样的按语:“从舒芜文章所揭发的材料,现在可以看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共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恨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
聂绀弩与夫人联名上书,强调“绝不可仅凭几封信中的片言只语便断定胡风为反革命分子”。
康濯亦指出:“在学术与理论之争中,若最终以个人间的通信内容作为反革命政治定性的依据,如今看来,此举实属不当。”
舒芜的登场,无疑成为中国当代思想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他率先开启了以私人信件作为“政治定性”的先例。舒芜被冠以新中国成立后首位公开“告密者”的称号。
舒芜对此并不认同,他进而举例说明,鲁迅在未曾获得授权的情况下,也曾公开发表过徐懋庸的信件,以此来佐证他“交信”之举的合理性。
有资料显示,舒芜把胡风的信件握在手中伺机“拿出去”的想法由来已久。舒芜后来曾说,他想抛信,是因为1954年7月听聂绀弩说胡风“当年发表《论主观》是为了批判”,一怒之下说:“我手里有他的信,拿出来可以证明事实完全相反。”而按梅志撰写的《胡风传》中的说法,舒芜当时对聂绀弩说的这句话是:“他别厉害,我手里还有他的信呢!”———由此可见,信件始终是舒芜押在手中的一个“法宝”,打出这个法宝是迟早的事。在胡风去世十二年后,舒芜又在1997年第二期《新文学史料》上发表的《〈回归“五四”〉后序》中,再次引用了胡风的另外三十七封信。为此招致胡风亲属们的指责:“……时隔四十多年后,在社会主义法制正逐步建立与完善的今天,舒芜先生仍旧如此行事,于法于理,都令人不能容忍!”
忏悔与悲剧终结
尽管舒芜对批判胡风之事贡献了所谓的“独特力量”,却并未受到应有的提拔与重用。他反而被视为“异类”,让人不禁感到几分畏惧。因此,他被指派至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核心刊物《中国社会科学》担任业务编审。1957年,他亦不幸沦为“右派”的一员,随之而来的是编审职称的剥夺和编辑室副主任职务的取消。“文革”期间,他遭受抄家与劳改的双重打击。
潮水退去,归于宁静,舒芜的内心却难以平静。尽管胡风家人曾明确表示“我们从未要求他忏悔”,舒芜仍深刻认识到“交信事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在《回归“五四”》、《舒芜口述自传》等作品中,他表达了自己的悔意:“虽非我所能预想,然而此事引发了一场巨大的冤案,无数人遭受迫害,家庭破碎,亲人离散,甚至有些人变得精神错乱,遭受了各种惨烈的命运。这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所有亲密无间的好友,尤其是那些一直支持、提拔、教导我的胡风。对于他们的苦难,我感到自己肩负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胡风出狱之际,周扬亲自造访其宅,紧紧握住胡风的手,诚挚地表示:“组织将承担一切责任,我对你深表歉意。”此外,周扬还在全国文联代表大会上公开发表道歉与忏悔,对胡风、丁玲等表示诚挚的歉意。
林默涵,一位亲历事件的见证者,感慨道:“胡风案件在文艺领域及社会层面引发了极大的波动,给受害者带来了无尽的痛苦。身为‘胡风事件’中的一员,我深感肩负着一份责任,对此亦深感懊悔。”
叶瑶,人民日报的女编审,坦言:“我同样不止一次地反思,在这起冤案中,我应承担何种责任?仅仅以‘奉命组稿’为借口,在道德层面难以自圆其说。诚然,我并无恶意伤害他人,这是事实。然而,疏忽也可能造成伤害,这一点难道可以否认?我的内心答案是肯定的。”
舒芜提及“文革”期间因“批孔”被卷入风波的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时感慨道:“杨国荣的悲剧,实乃社会历史的必然。数十年间,我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哪怕那些自诩为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者,又有谁能真正掌控自己的命运呢?他们无不受到命运的捉弄,不知不觉中成为了被利用的棋子。”显然,舒芜在同情他人不幸命运的同时,也对自己的人生轨迹有所感慨。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番话出自他内心深处。因为他对于胡风事件已有深入的反思之久了。
舒芜等人纷纷提及“责任”一词,然而,事过境迁,再对“责任”进行讨论,实则已无实质性意义。倒是那个“利用”的概念,值得我们深思。

